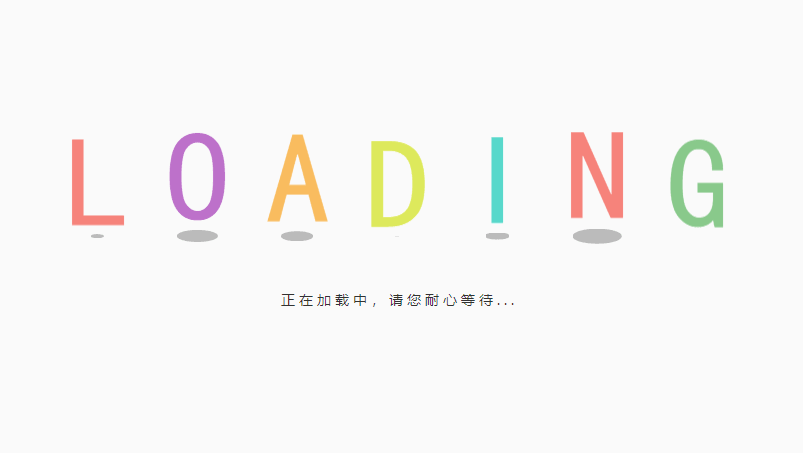“请托”实质上是一种什么行为?“请托之风”的盛行造成的影响?
|
盐商利用经济手段对明代文人创作的参与主要是通过“请托”来实现的。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说“明代文学表现商人的一个基本特色,就是不仅通俗文学大量与广泛地表现了商人,而且传统诗文也不亚于通俗文学,翻开任何一部明人文集,几乎都能看到若干与商人有关的作品。 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也为以后所少见。”他还指出,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中,“经济因素也许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重要。”余英时也认为:“文人谀墓取酬,自古有之,但为商人大量写碑传、寿序,则是明代的新现象,明代不少士大夫(如在中央任清要之职的人)往往要靠润笔来补贴生活费用。”经济因素在文人与盐商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邵毅平所说的经济因素,其实也就是明人俗谓“请托”者,即商人通过向文人支付可观的润笔费,雇佣文人为商人本人或其家属撰写文章(主要是碑传、墓志铭、寿序等文体)。请托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行交换的行为。 这种交换不一定是以金钱的形式,也可能是以人情进行交换,焦竑《国朝献征録》记载:“有蔡生请盐商墓志不获,同寮为之请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吕柟)曰,一书生而遨游权贵之门,得志则下陵可知。”而盐商之子程开禧为自己母亲向钟惺请托的方式则是以诗为贽:“新安有程太学凝之讳开禧者,善诗,自淮上介友人郝子荆,以诗请于予,读之惊叹得未曾有。
子荆曰,未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问何物,曰凝之母昝孺人行实也,予笑曰程子欲以诗贽予文乎,以诗贽文,类相从也,遂志之。”盐商虽不是请托风气的始作俑者,但却是请托风气的忠实拥趸者。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扬州盐商“此辈到处请托,至今南都人语及之,即以为谈柄”,表现了当时盐商到处请托,引起相当一部分士人反感的社会现象。据今人张敏《明中期文人别集中商人传记文献研究》统计,在写明传主所经营行业的59篇商人传记中,有21篇是盐商,占35.6%,是占比最高的商人种类。这组数据足以说明盐商对于“请托”之事的狂热。
“请托”的盛行直接导致明代文人别集中的盐商行状、传记、墓志铭等应酬文体的爆炸式增长,其中不乏出自当时一些著名文人之手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是为应付请托创作,因而在内容上充斥着对传主的溢美之词,相较于创作者其他作品而言,这类应酬文字文学价值是比较低的。但在这些作品中却也不乏寄托着作者真情实感,人物塑造饱满生动的优秀之作,如王世贞《罗山汪次公䀈继配杜孺人合葬志铭》讲述了被盐商一致推举为“盐筴祭酒”的盐商汪良植的生平,表现了他游走京城化解众商危机、面对歹徒抢劫临危不惧感化歹徒、只言片语化解两家竞争对手的恩怨使之重归于好的领袖风度。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很多的笔墨描写了他与妻子杜氏忠贞不渝的爱情与相濡以沫的温情,记叙丧妻之后汪良植对亡妻的思念。在他的女儿选择守节殉死后,“次公虽宽襟豁落,与伯季及左司马觞而快然不能,不时慨然曰:‘吾殇子女多矣,独不忍于洪之嫠方之殉,柰何凡以女徳显者,非其家福也’”。 汪良植饮酒之时,忽然想起女儿,难掩对女儿的痛惜与追念。这一情节,使人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王玉辉“一路看着水色山光,悲悼女儿,凄凄惶惶”,深受礼教毒害而又难掩慈父心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令人唏嘘。作者通过一系列曲折生动的事迹,使读者看到了汪良植从早期“少年游”时的意气风发到丧妻丧女后的借酒消愁,既胸怀磊落又儿女情长,充满人性的温度,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发展性和多面性,因而十分饱满。
虽然许多文人对于这股请托之风颇为不满,为商人撰写过15篇传记的王世贞,私下曾经向朋友抱怨:“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明代以前的文学已经给盐商打上了许多负面标签的情况下,“请托”确实为当时文人接触并了解盐商正面品格提供了一个契机,即如王世贞为汪良植所写的传记中,称他“古所称磊落大丈夫者,其汪次公哉!” 也绝非违心之语。汪良植在默默无闻的小盐商之时,便躬行仁义,在成为大盐商后,也依然保持着磊落的人格,这使王世贞认识到仁义与富贵与否无关,“必富而后仁义附,则次公当泯泯不振矣。”只要躬行仁义,无论贫富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对于汪良植的尊重与褒扬,反映出明代文人对于盐商的看法不再是一昧贬斥,而已有所转变。
请托之风一直贯穿了整个明代中后期,最为盛行之时,大约是明代正德、嘉靖时期,传主大多为第一代第二代盐商,他们经历了白手起家的艰难,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交游感到有心无力,需要通过请托这一形式发展他们的社交网络,却也因此常受到附庸风雅的讥刺与非议。而明代万历以后,盐商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已经逐渐形成,许多盐商家族发展到三代以上,家族资本达到相当规模。 这些三代盐商们从小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家族世代累计的资本使他们不必如他们的祖辈父辈那样忙于行商,又接受了比祖辈父辈更为优渥的文化教育,因而他们有更加充裕的时间、金钱与能力参与到文学活动之中,“新安多大贾,其居盐䇲者最豪。入则敲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非不足也。”请托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文学的需求,因而一些盐商将目光投向需要更多资金投入,也更具娱乐性质的文学活动之中,例如戏曲与诗文**。
明代盐商尤其钟爱戏曲,而且也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戏曲活动之中,如歙县盐商潘侃(潘汀州)一生酷爱戏曲,“诸倡乐有至者,辄留为汀州公欢嚎。”其子潘君南“亦复好广宾客,诸博徒蹄跳技击倡优杂戏,如汀州公”,在其父八十寿辰之时,他还专门从江淮带了演员回家为父亲祝寿;盐商汪宗孝在金陵时,蓄养了许多年轻有资质的少女,教以歌舞与戏曲,“翠屏绛帐中香气与人声偕发,若莺凤鸣烟云间”。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载万历时徽州休宁一次戏曲活动,结果变成了各盐商巨贾相互攀比炫富的舞台:“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共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故事,饰以金珠增彩,竞斗靡丽美观也。有劝以移此巨费,以娠贫乏,则群笑为迂矣。”这种堪称夸张的奢华,到了清代更加登峰造极,徽州盐商对戏曲的狂热与痴迷由此可见一斑。他们不仅热衷于欣赏戏曲,也通过培养家班等方式,亲自参与到戏曲活动之中,汪季玄便是当时颇为知名的盐商戏曲家。 |
相关文章
热销商品

淘Yukiss 小个子羊毛呢料高腰西裤短裤女冬韩系修身叠穿气质休闲裤
Yukiss 小个子羊毛呢料高腰西裤短裤女冬韩系修身叠穿气质休闲裤
¥118 领券购买
淘COLDSTONE 阔腿弯刀西裤垂感百搭休闲复古显瘦高级女春夏新款长款
COLDSTONE 阔腿弯刀西裤垂感百搭休闲复古显瘦高级女春夏新款长款
¥148 领券购买
淘黑色微喇西裤子女款爆款2025新款秋冬加绒显瘦垂感弹力百搭喇叭裤
黑色微喇西裤子女款爆款2025新款秋冬加绒显瘦垂感弹力百搭喇叭裤
¥69.9 领券购买
淘ZONEE/LEA宋亦雯 圣诞鎏金 法式精致时髦感粗花呢小香休闲短裤女
ZONEE/LEA宋亦雯 圣诞鎏金 法式精致时髦感粗花呢小香休闲短裤女
¥316.36 领券购买
天香港直邮Hermes爱马仕大地男士淡香水木质香清新明亮50/100ml正品
香港直邮Hermes爱马仕大地男士淡香水木质香清新明亮50/100ml正品
¥308.63 领券购买
天【李治廷同款】Boitown冰希黎仕界淡香持久留香水木质香送男友
【李治廷同款】Boitown冰希黎仕界淡香持久留香水木质香送男友
¥158 领券购买
天Bon Parfumeur柏氛602香水EDP清冷雪松秘境木质香调生日礼物男女
Bon Parfumeur柏氛602香水EDP清冷雪松秘境木质香调生日礼物男女
¥229.6 领券购买
天马登2026新款复古灯芯绒高帮板鞋男潮流百搭低帮休闲帆布鞋子
马登2026新款复古灯芯绒高帮板鞋男潮流百搭低帮休闲帆布鞋子
¥149.9 领券购买
淘超声波洗碗机商用全自动餐饮饭店食堂餐厅用多功能大型小型洗碗机
超声波洗碗机商用全自动餐饮饭店食堂餐厅用多功能大型小型洗碗机
¥1150 领券购买
天美的万向变频洗碗机家用全自动烘干消毒一体嵌入式18套X6SMax官方
美的万向变频洗碗机家用全自动烘干消毒一体嵌入式18套X6SMax官方
¥5292.94 领券购买
淘3罐】风干鸡胸肉干条蛋白健身宿舍耐嚼装即食手撕休闲解馋零食
3罐】风干鸡胸肉干条蛋白健身宿舍耐嚼装即食手撕休闲解馋零食
¥4.9 领券购买
淘陈阿炳风干鸡肉干官方旗舰店手撕鸡肉条鸡胸肉过年年货零食新年
陈阿炳风干鸡肉干官方旗舰店手撕鸡肉条鸡胸肉过年年货零食新年
¥24.7 领券购买
淘茶杯消毒柜小型办公室茶具茶道专用烘干收纳水杯子功夫茶台式迷你
茶杯消毒柜小型办公室茶具茶道专用烘干收纳水杯子功夫茶台式迷你
¥289 领券购买
天康宝ER630家用嵌入式消毒柜120L热风二星母婴烘干消毒不锈钢板架
康宝ER630家用嵌入式消毒柜120L热风二星母婴烘干消毒不锈钢板架
¥1998 领券购买
天G2000男装2025秋季新款商务经典质感衬衣易打理职业上班长袖衬衫.
G2000男装2025秋季新款商务经典质感衬衣易打理职业上班长袖衬衫.
¥169 领券购买
天2026新款语音ai人工智能编程机械狗玩具遥控机器狗儿童男女孩仿生
2026新款语音ai人工智能编程机械狗玩具遥控机器狗儿童男女孩仿生
¥96 领券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