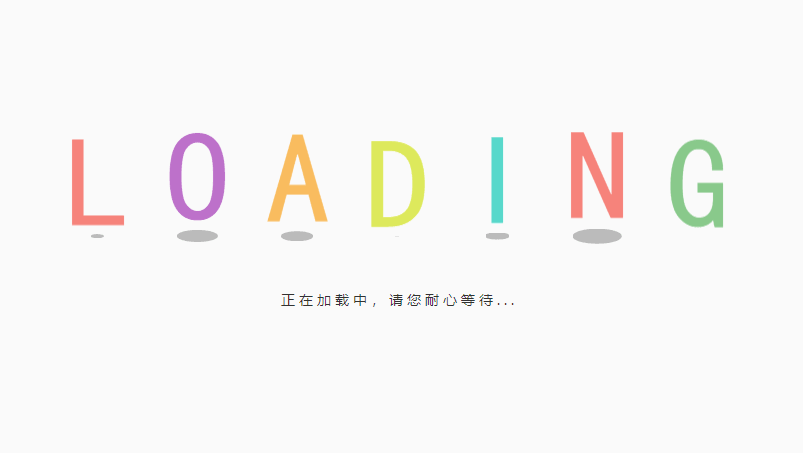元代宗王附属机构对非势力范围地区的干预方式是什么?
|
在元代分封制的运作过程中,宗王不仅满足于对自己所控制地域内的事务管理,而且想方设法干涉其他地区内的各项事务,本章便是以此为出发点,探究元代宗王及其附属机构对非势力范围事务的干预。 学术界在研究元代诸王对地方施加的影响时,往往着眼于其势力范围内,即兀鲁思封地、五户丝食邑、宗王镇所、投下私属部民、朝廷拨赐,而对于本章研究的问题涉及甚少。而实际上,有元一代,宗王及其附属机构对非势力范围地区的干涉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单独讨论。本文通过研究宗王干涉非势力范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为元代分封制度优缺点和实际运作情况、宗王与朝廷和地方的关系等提供了新的视角,完善前人研究的欠缺之处,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对非势力范围行政、司法的干预元代宗王附属机构对于非势力范围的司法干预,可通过有关碑刻史料,加以探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灵岩寺执照碑》拓片,此碑体现了晋王内史府对地方司法案件的干预,对于原告和被告的处理上,此案件有宗王势力的参与,以致出现了司法上的问题。
延祐二年(1315)三月初一,内史府官员李忠显携带圣旨前来,“开读讫,除钦遵外”,命令灵岩寺僧人将九曲峪的土地“吐退”,在被拒绝后,李忠显去往长清县,“令本县官司行发信牌,将思让等勾扰不安,告乞施行”,于是便有了碑文开头灵岩寺僧人当官告称:“累累被前煽炼人等,于本寺山场内搔扰不安,诚恐已后引惹事端,告乞施行”。关于信牌的执行者究竟是谁,还是有争议的,业师杜立晖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元代信牌使用人员庞杂,凡是纳入元朝官府管理的官吏、衙役、公使人、差役等人员,都有权使用信牌。
船田善之先生认为信牌便是县政府直接发放给内史府使臣李忠显的,李忠显便为信牌的直接使用者,但灵岩寺执照碑行文简洁,并没有直接说明此事,另外一个可能便是此信牌是在李忠显的授意下,由长清县发放,再由地方官吏凭此勾唤僧人的,毕竟信牌的使用者从《元典章》的记载可以看出,其多为“差官并随衙门勾当人曳剌、祗候人等”,甚至部分里正、主首等差役也有信牌的使用权,而且从碑文内容看,为“道罢,本官前去长清县,令本县官司行发信牌,将思让等勾扰不安,告乞施行”,其中“本官”即为李忠显,李忠显命令县司发放信牌,骚扰僧人。
无论如何,信牌的接收者是没有疑问的,便是灵岩寺僧人,又由此引发了疑问,也就是说前期灵岩寺莫名其妙处在了一种接受信牌的“被告”地位,而碑刻却没有记载内史府状告灵岩寺的事情,只是使臣在宣读完圣旨后提出了让灵岩寺“吐退”矿冶的要求,之后便是指使县官府发放信牌。若内史府的诉求合法,完全是可以按照正常的司法手续状告灵岩寺的,而非不经手续便直接判断灵岩寺“侵占”其矿冶,再进行发放信牌的流程,这也说明了内史府的要求“吐退”的行径本身是无理的,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手续进行,而是通过直接干预县官府发放信牌的方式妄图暗地里达成目的。 另外,案件后期经过灵岩寺僧人状告后,内史府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被告的地位的,但县官府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没有按照规定传唤内史府相关人员,换言之就是说此案件并没有记载司法手续中对被告进行的勾唤,无论在县级官府还是行省级官府都未出现内史府作为被告的身影,直到中书兵部判决时,才“照勘”知会内史府,以此可看出宗王附属势力在地方上的强势地位。
以上内容可见,此案件出现了被告地位的反转,灵岩寺僧人先是莫名成为“被告”,后虽作为原告的身份出现,但应有的司法程序自始至终都未真正进行。其原因在于晋王势力的干预,地方的行政司法出现了问题。此处的地方指的是与宗王并无直接关系的非势力范围地区,因在规定层次上山东地区与晋王并无直接关系,史料中唯一能够见到的有所关联的是镇守益都、济南的阔阔不花经朝廷整顿后其子东哥马投献给甘麻刺的“二百七十五户”益都畸零”,而且此部民皆为五户丝,并不涉及矿冶事。 从灵岩寺执照碑案件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出内史府官员是能够直接命令县级官府的,而且通过船田先生所举考古发现说明晋王在山东确有矿产存在,这又说明晋王一系侵吞了非势力范围的经济利益,内史府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估计也是为了维护和进一步扩大其在山东地区的矿产。
综上可以看出,晋王干涉地方行政司法的方式是派遣其附属官员去往山东而不是直接通过正规的渠道层层传达,因山东并非是其势力范围,在内史府使臣的干预下,地方行政司法出现了严重问题,常规的司法手续遭到破坏,还引发了地方寺院的混乱,其干涉司法的真正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晋王原本就侵吞的地方经济利益,而由于地方寺院僧人的不妥协和二次状告,使得此案件引起重视,甚至逐级上报到中央机构,针对宗王使臣干涉地方行政司法的现象,中书兵部做出判决,使得宗王的干涉未达到想要的结果。
按《元史》等史料所记载,自汪古部归顺后,太祖成吉思汗便以公主阿刺海下嫁给首领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后追封高唐王。其后汪古部得以与黄金家族的诸王之女“世缔国姻”,其侄镇国收继阿刺海公主,获封北平王,生有一子,名为聂古台,袭父爵,即尚睿宗拖雷之女独木干公主。 但聂古台略地江淮时死于军中,且无嗣,得赐兴州民千余户以葬”,如同阿刺海以“监国公主”的身份管理汪古部,独木干公主此时便已主持其部下各项事务。据此碑所记载,刘仲“钦奉懿旨”的时间是乙巳年(1245),周清澍先生认为,壬子年清查汪古部户口时以孛要合次子爱不花的名义代表汪古部,以及同年独木干公主加封西京大华严寺和尚徽号,说明此时聂古台已死,而此碑的记载将时间往前推进,说明独木干公主掌权时间更早。
对此,独木干公主于丁已年(1257)方才得赐平阳路五户丝一千一百户,即便是其监管汪古部的领地,其势力范围也应在汪古部领地内,也就是蒙古大举攻金后所获取的兀鲁思,据至元八年(1271)的文书记载,壬子年(1252)清查“爱不花驸马位下人户”时,有“砂井、集宁、静州、按打堡子”四处。 对此,周清澍先生详细考察了其领地建制”,总体上位于阴山南北,黑水附近。其五户丝食邑在乙巳年(1245)之前有阿刺海东平府户拨赐、高唐州两万户、夏津、武城二县”,高唐县属博州,夏津县属大名府,武城县属恩州,后同属于高唐州,再加上聂古台死后给葬的兴州,可以确定的是此时汪古部的势力范围并未涉及到山西地区。 |
相关文章
热销商品

天暗夜黑立领PU皮衣外套女MOFAN摩凡2025秋冬酷飒风皮夹克短款显瘦
暗夜黑立领PU皮衣外套女MOFAN摩凡2025秋冬酷飒风皮夹克短款显瘦
¥299 领券购买
淘落落狷介 黑色皮衣女机车外套设计感小众加棉冬季PU皮外套小个子
落落狷介 黑色皮衣女机车外套设计感小众加棉冬季PU皮外套小个子
¥403 领券购买
天MOUSSY 2025秋季新品潮酷时尚简约拉链皮衣外套女028IAC30-1069
MOUSSY 2025秋季新品潮酷时尚简约拉链皮衣外套女028IAC30-1069
¥1049 领券购买
淘狂神排球KS0884中学生中考试专用5号训练皮质球男女软式初学者
狂神排球KS0884中学生中考试专用5号训练皮质球男女软式初学者
¥37 领券购买
天奥匹排球中考学生比赛充气软式5号球标准训练球初学者沙滩硬排球
奥匹排球中考学生比赛充气软式5号球标准训练球初学者沙滩硬排球
¥49 领券购买
天全棉三层纱床单单件A类母婴级100纯棉亲肤提花宿舍被单枕套三件套
全棉三层纱床单单件A类母婴级100纯棉亲肤提花宿舍被单枕套三件套
¥62.56 领券购买
淘胖mm300斤特大码设计感假两件钉珠卫衣女秋冬200洋气宽松长袖上衣
胖mm300斤特大码设计感假两件钉珠卫衣女秋冬200洋气宽松长袖上衣
¥87.1 领券购买
天雪中飞2025秋新款羽绒马甲薄款90%鸭绒无袖马夹温暖内搭拉链男装W
雪中飞2025秋新款羽绒马甲薄款90%鸭绒无袖马夹温暖内搭拉链男装W
¥299 领券购买
淘中老年男式加绒加厚背心爸爸冬季保暖坎肩纽扣款无袖开衫马甲宽松
中老年男式加绒加厚背心爸爸冬季保暖坎肩纽扣款无袖开衫马甲宽松
¥54 领券购买
淘YANGLE_牛仔裤女2025新款秋冬抓绒藏青色休闲宽松显瘦窄版直筒裤
YANGLE_牛仔裤女2025新款秋冬抓绒藏青色休闲宽松显瘦窄版直筒裤
¥218 领券购买
淘2025女装灰色冬季针织辣妹打底短裤秋季显瘦高腰修身百搭休闲裤子
2025女装灰色冬季针织辣妹打底短裤秋季显瘦高腰修身百搭休闲裤子
¥17.5 领券购买
天三丽鸥话筒音响一体麦克风蓝牙儿童K歌小音箱家庭KTV生日礼物无线
三丽鸥话筒音响一体麦克风蓝牙儿童K歌小音箱家庭KTV生日礼物无线
¥51.9 领券购买
淘多功能两用胸包男女户外出行旅游轻便小型双肩包防水登山包斜挎包
多功能两用胸包男女户外出行旅游轻便小型双肩包防水登山包斜挎包
¥31.6 领券购买
淘加厚帆布旅行包男士大容量结实耐用女手提行李包可套拉杆箱旅游包
加厚帆布旅行包男士大容量结实耐用女手提行李包可套拉杆箱旅游包
¥13.8 领券购买
天旅行包女轻便可套拉杆箱短途行李袋健身手提包孕妇入院待产收纳包
旅行包女轻便可套拉杆箱短途行李袋健身手提包孕妇入院待产收纳包
¥32.4 领券购买
天七匹狼男士内裤男生纯棉平角裤全棉透气裤衩男式大码四角裤短裤头
七匹狼男士内裤男生纯棉平角裤全棉透气裤衩男式大码四角裤短裤头
¥52.7 领券购买